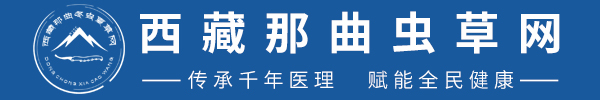草原上的神奇蜕变:我眼中冬虫夏草的形成
在藏北那曲的草原上,我放了四十多年的牦牛,也跟着阿爸、爷爷采了三十多年的冬虫夏草。老辈人常说,虫草是雪山神赐予牧民的珍宝,它既不是草,也不是虫,是草原上最特别的“活物”。这些年,我看着雪山下的草甸枯了又绿,也慢慢摸清了这宝贝从“虫”变成“草”的门道,每一步都藏着草原的规矩和自然的神奇。
每年入秋,草原上的风开始变凉,夜里能结出薄霜的时候,虫草的故事就开始了。我们牧民都知道,这时候草原地下藏着一种叫“蝙蝠蛾”的虫子,它们从卵里孵出来后,会在土里钻来钻去,啃食草根长大。这虫子比我们的小指还细,浑身是白白的肉,在土里要待上两三年,就等着冬天到来,变成蛹,再羽化成飞蛾。可偏偏草原上还藏着另一种“看不见的力量”——虫草真菌的孢子,它们像草原上的细沙,悄悄落在土里,一旦遇到蝙蝠蛾幼虫,就会钻进虫子的身体里。

我阿爸年轻时总说,这是“真菌和虫子的约定”。真菌孢子钻进虫体后,不会立刻杀死虫子,而是慢慢吸收虫子身体里的营养,就像草原上的牦牛吃青草一样。这时候的虫子还活着,却已经被真菌“控制”了——它会不由自主地往土壤深处钻,大概要钻到离地面十几厘米的地方,那里的温度刚好,不会太冷也不会太热。等冬天的大雪覆盖草原,土层结了冰,虫子就会停止活动,真菌也放慢生长的速度,它们就这么在冻土下“睡”着,等着春天的到来。
第二年开春,雪水顺着草甸的缝隙往下渗,冻土慢慢融化,草原开始冒出新绿的时候,真菌就会从虫子的身体里“醒”过来。它会顺着虫子的头部,慢慢往上长,穿过土层,最后冒出地面,长成一根细细的、棕褐色的“草”——我们叫它“草头”,草头顶端还会结出小小的孢子囊,等风吹过,孢子又会落到土里,开始新的循环。而那只曾经的蝙蝠蛾幼虫,身体已经变得僵硬,外壳紧紧包裹着真菌的菌丝,就像给“草”做了个“虫形的根”,这就是我们挖的冬虫夏草——下面是虫的身子,上面是真菌长出来的“草”。
这些年,我在采挖的时候,总能发现一些有趣的细节。比如虫草的“草头”冒出土面时,大多是朝着向阳的方向,因为那里的土层化得快;还有,如果当年的雪下得大、融得慢,虫草冒头就会晚一些,而且虫体也会更饱满——雪水滋润了草甸,真菌长得好,虫子的营养也足。但要是遇到干旱的年份,土里的虫子少,虫草也会变得稀疏,有时候在草甸上趴一整天,也挖不到几根。
老辈人常告诫我们,挖虫草的时候要轻手轻脚,把虫草周围的土慢慢拨开,不能弄断虫体和草头,挖完后还要把土填回去,把草皮拍平。他们说,虫草是草原的一部分,不能贪心,要给草原留着“念想”,这样来年才能再长出新的虫草。我想,这大概就是虫草的“脾气”——它依着草原的季节生长,靠着自然的规律蜕变,也需要我们牧民用心守护。
现在,我也会带着家里的孩子去草原上认虫草,教他们看草头的颜色、辨土层的湿度,告诉他们这宝贝是怎么从一只地下的虫子,变成草原上的珍宝。在我眼里,冬虫夏草不只是能换钱的药材,更是草原四季轮回的见证,是自然和生命的神奇约定。
免责声明:该内容来源于网友提供或网络搜集,由本站编辑整理,如涉及版权问题,请联系本站管理员予以更改或删除。
更多阅读